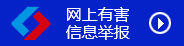去年在这开会的时候,十八大还没有召开,改革形势还不太明朗,一些同志有点担心。当时我的看法比较积极,“满园春色关不住”,讲的是会场外面的景象。当时只有个别的桃花开了,但是我想改革的新阶段就要开始了,满园春色是关不住的。今年春天来得早,从自然景象来看,已是春意盎然。但是从改革发展看,作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忧虑,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和改革的关系,二是顶层设计和改革主导权部门化的关系,三是大胆探索、突破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因时间关系我重点讲讲第一个问题,也与今天的主题“宏观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呼应起来。
第一,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一季度马上就要过去了,近一时期,国内外专家,国务院各部门,直至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度关注当前的宏观形势。总书记在“两会”预备会上讲到稳中求进的同时,也讲到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人大财经委在审议计划报告的时候,张德江委员长专门又加了一句“稳增长是当前最艰巨的任务”。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结束,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讲到“不唯GDP,但是增长的弹性也一定要服从于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是对经济的走势给了一个下限。
目前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是最严峻的挑战。1-2月份各个指标下行比较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月份增长17.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月份增长11.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5%;外贸1-2月份波动比较大,增长3.8%,比去年同期增幅下降10.4%;工业增加值是8.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从指标来看,一季度GDP年化率就是7%多一点。工业由于前一段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河北省的工业增加值只有3.5%,山西只有5.1%,黑龙江只有0.3%。如果工业增加值只有0.3%,那么经济增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关注的领域还有房地产。房地产一边连着土地财政,涉及到地方债务的问题,一边联系到银行贷款和金融风险问题。很不幸的是,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类似“断崖”的现象。去年1-2月份商品房的销售额增长了77.6%,全年增长了26.3%,但是今年的1-2月份商品房的销售额下降3.7%,如果做一个曲线图可以看出是一个多么陡的曲线。从商品房销售面积来看,去年1-2月份增长了49.5%,全年增长了17.3%,今年的1-2月份下降了0.1%。从房价来看,去年1-2月份房价同比涨了18.8%,全年涨了7.7%,今年1-2月份下降了3.6%。这些现象,反映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把“全面深化改革”和“稳增长”作为目前面临的双重挑战和任务,这就又回到多少年讨论的老话题——发展和改革的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讲,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但是从短期来看,如果把“稳增长”的问题提到一个不必要的高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改革的信心或影响改革的总体部署。
回到今年的GDP增长指标上。今年定的GDP增长指标是7.5%左右,而且一直在强调是个预期性的指标。但是我感觉从计划指标特别是增长指标的制定上,我们还没有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比较多考虑的是从政府的主观意愿,从增长速度的必要性来确定增长的目标。一般对定在7.5%左右的解释,主要是考虑居民收入的增长、就业的安排和结构调整和其他稳增长的需要,主要强调的是必要性。
但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不一定这样确定指标。如果有这样一个预期性的指标,应该考虑市场的需求到底是多少,潜在的增长率是多少,就是一个市场可能性的分析。我们还没有转到市场经济的思维角度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和有关部门讨论计划报告和今年要启动“十三五”规划时提出,很重要的一条是指标体系怎么确定和搭配,才能总体上符合市场经济和当前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需要。举例说,去年投资增长是19.3%,今年计划调到17.5%;商品销售总额也就是消费,从去年的13.1%调升到今年的14.5%。消费方面的指标上调能不能弥补投资下降所带来的空间?有一些搞理论和模型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外贸去年增长7.6%,今年计划增长7.5%左右,变化不大,关键是投资和消费这两块的转换能不能实现。但是很不幸的是商品零售总额实际上在逐年下降,2010年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8.3%,2011年增长17.1%,2012年14.3%,去年13.1%,今年一开局只有11.8%。所以靠现在的最终消费,如果没新的有热点的话,要满足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很难的。最后稳增长还是要依靠投资,就会回到传统增长模式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地方。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一步淡化GDP增长的指标,同时增加对增长弹性的容忍度。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如果把今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实事求是的定在7%左右,就非常主动了。但是现在也不迟,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总体需要,如果真的能从概念上改变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性指标的定义的话,以后能不能做一点大的调整?比如由做宏观模型的研究部门发布经济增长的预测,这种指标每个季度还可以做调整,这样实实在在地把经济增长指标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性宏观工具,而不是现在名为政府预期性指标,但实际上都是拼命要完成的硬指标。
第二,关于按照问题倒逼法考虑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去年在这讨论形势的时候,当时我也讲到下一步的改革无非是三种路径选择:一是问题导入法,二是目标迫近法,三是乘势而上法,就是跟着感觉走。但是最后大家看得比较明确,中央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按问题导入法,也就是矛盾问题倒逼产生的。哪些问题阻碍了当前的生产力,哪些改革就要做优先的考虑,当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提升经济的内生动力,使经济有活力有希望。但是活力和希望在哪里呢?我觉得不是政府是市场,不是国企是民间资本,所以改革很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提供公平、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
大家看一看计划报告,里面也讲到要在金融、电力、铁路、电信、石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方面推出一些示范性的项目,可能先找个突破口。大家听起来很受鼓舞,但是落实的话,我觉得还不够,不能激发社会市场的活力和大家投资的积极性,要真正下决心拿出一些垄断行业。一是破除一切行政性的垄断,二是打破一些自然性垄断。自然性垄断行业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加强监管的思路,可以先重点在特许经营上开个口子,特许经营不仅是国企可以进入,民间资本也可以平等进入。
实际上大家比较关注的严重产能过剩的领域都是过去国家管得比较严格的。这些行业不是垄断行业,而是竞争性的行业,但是国家管得严格。严格的结果是什么?河北将近3亿吨的钢铁产能,国家批的只有7000万吨,有色金属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真正建立市场化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不能把它放开?管也没管好,还不如放开市场,政府把技术标准、环境门槛等问题定扎实,前置审批该放开的放开,注重事后的监督。在清理过剩产能、增强投资责任的情况下放开市场管制,这是很好的契机。
放开市场后虽然企业不会马上增加投资,但是给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市场化改革。像石油进口为什么民营不能搞?还有盐业改革方案搞了多少年现在还维持着盐业专营。我觉得有些要考虑的比较成熟,有的是要抓住时机推出一批真正能够传达我们改革决心,同时有利于调动市场投资热情、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这个可能是现在急需要做的。
另外,收入分配的改革喊了多年,去年年初上届政府决策推出的最后一个文件是《关于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的出台历经波折,原来讲的是以“两办”的名义发一个决定,后来改为以国务院的名义发,最后变成了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保部等几个部门联合发的文件。但是《意见》出来以后又没有下文了。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城乡居民和经济增长同步中央几次全会都讲到,但是始终是做不到。今年年初计划报告还讲,今年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但我们是不同意的,中央讲的是“两个同步”,为什么加个“基本”?加个“基本”整个意思就变调了。
去年的指标统计确实做不到两个同步。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7%,农村居民收入高一点,是9.1%。但是2013年的经济增长是7.7%。最后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统计概念——城乡居民收入。原来只有“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现在创造出新的概念“城乡居民收入”,平均了一下是8.1%,高于7.7%。这样在理论上讲,我们还是实现了“两个同步”。
昨晚景安同志到我那儿聊天,谈到执政理念问题。现在执政理念强调的还是发展,而不是民生。发展是为了什么?如果大家都是搞GDP、搞投资、搞项目,忘了发展的最终目的,居民的收入没有增加,我们的经济转型往哪转?就转不了。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回到中央《决定》已经明确讲过的“两个同步”。另外要提高劳动收益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三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整个居民财产性的收入,包括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又涉及到土改问题。现在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增加?实际上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土地。我们要破局,要解决目前稳增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可能还是要回到用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子上。通过一些深化改革真正大胆的突破,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和问题。时间关系我今天重点讲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改革主导权部门化的关系等问题,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