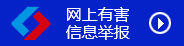作为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转轨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当时,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转轨经济学与“制度变迁”(古典制度经济学当中描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过程的概念)的差别在于,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发生时,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向、要向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转变。而“转轨经济学”描述的是从一种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种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转变的过程。
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要去彼岸,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仅在于如何过河,所以要摸着石头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细节我们可能也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当时出国访问过的领导人们知道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市场”这个概念很早就作为一个目标模式提出来,是能说明很多问题的。
这也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历史上很特殊的制度变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批国家开始了体制转轨的过程,用简单的归类法,可以说存在两种不同的转轨方式,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另一种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那么,两种方式有没有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别,首先在于旧体制的覆盖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几乎9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有计划部门,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加入了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1978年的中国,国有部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60%,享受统一社会保障的只有占劳动力总数18%左右的国有企业职工。在俄罗斯,如果不改革国有部门,把劳动力和生产力释放出来,非国有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在中国,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在非国有的农业部门,只要实行了农业改革,允许乡镇工业和服务业在市场上发展,就可以在先不进行国有部门改革的情况下,就开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通过“双轨制”的方式,使新体制成长起来,逐步为改革旧体制创造条件。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发展阶段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苏联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而1978年的中国仍属于一个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制度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展开。俄罗斯尽管开始阶段会有较大的阵痛,却相对容易引入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可以较快地实现转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别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别。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背景的差异。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欧洲国家,宗教、文化、政治、法律,与西欧和北美有着诸多的共性,可以较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或实现“知识外溢”,比较容易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移植西方的制度。而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与西方有着太多根本性的差异,从政治制度到宗教文化,走过了极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转轨,而是一个大方向基本明确前提下的“适应性体制创新”。几百年后,各国的制度可能趋同(西方国家也一定要不断改革和调整),但是各国走过的路径,却可能因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各不相同。
总之,确实存在一些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东西,确实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轨。差别主要在于各国的起始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背景不同,而不在于孰优孰劣。
就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别在于:俄罗斯是一个经济已经较为发达的国家实行制度改革,而中国既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体制转轨国家。正因如此,我们要充分估计中国“双重使命”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没有发展,我们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善,而没有制度变革,我们的发展就会因效率低下而困难重重。
中国一个重要的后发劣势在于,人们往往会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制度缺陷,并不认真思考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许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同样存在过,但是当下的人们不会进行这种历史的比较,而是每每做着当下“横断面”的直接比较,由此提出各种超越历史的诉求,各种“大跃进”或“体制赶超”的主张就会层出不穷。作为经济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在于提醒人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直面一个落后国家可能面对的发展与改革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积极推动改革,同时坚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走过我们必须走过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