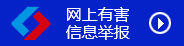我简单讲几句话,听到很多过去无法听到的东西,因为我是搞信息的,基本上观察都是草根阶层的观察,不像在座各位领导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见到领导人进行交流汇报。
从草根观察看,改革的趋势不容乐观,基本前提条件讨论尚不充分。谈到改革问题,尤其是突破口的问题,宋会长提到春潮涌动等等令人心潮澎湃的说法。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没这么乐观,尤其是基于这些草根观察得出的结论,感觉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一些基本的假设条件,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没有涉及到,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去谈改革、谈方案、谈各种各样解决的路径恐怕就不会是很现实的,不会得出很现实的结论。
一个是怎么做的问题,一个是做什么的问题。做什么的问题、方向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沟通,没有得到社会舆论和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谈能解决什么问题恐怕就有很大的疑问。无非是一拨人说我的制度比你的制度好,我的方案比你的方案好,后一拨人否定上一拨人的方案,无非是这样的过程。一些根本性的假设要讨论,一些根本性的前提要讨论,这是逻辑展开和程度上的深入所必须具备的。当然这会涉及到一些思想解放的问题,任何改革不涉及到思想解放,这个改革是什么程度上的改革,肯定是有很大疑问的。
举几个例子谈改革的根本问题和基本的假设条件。
比如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就不谈了,因为刚才很多的学者都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就谈谈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我们是回避不了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经过充分的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可能也不会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支持度比较高的结论。国有企业认为自己就是个支柱,它的垄断是有理由的,有基于先天性的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的支配下各种各样的话都能讲得出来,在一些大型的企业网站上挂着很多耸人听闻的,自我追封的“地位”和“说法”。像这种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上午讨论当中涉及到金融体系为国有企业服务等等问题,这些基本上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的问题。根本问题在国有企业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是支柱还是怎么样?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谈不上公平,谈不上多大程度上的公平,至于市场实际也就谈不上了。
制造业地位和工业发展现代化的模式遭遇巨大的困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我们究竟怎么看制造业?外国人看中国主要看的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连加工贸易的地位都成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不重要。世界工厂也好,制造业也好,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很多了,但却没有得到客观的、一致的看法,很多人实际上就是已经认为制造业是不重要的。
城镇化也是一个问题,何去何从还没有一个清晰路径,一方面要大力去搞,另一方面又没有路径,靠瞎猜,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曾经对现在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各种可能性做过分析,整理出路线图的研究报告,估计可能新型城镇化的走向还是走向产业化和乡镇基础上的城市化。过去比较强调土地拿过来以后,不管用什么广东模式、浙江模式、成都模式,反正拿过来以后搞房地产。今后城镇化可能会回归到搞产业,搞各种各样的工业项目,如果说制造业的地位和工业发展模式的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共识,那么在经济增长当中,城镇化在经济大盘子当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也不会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放任地去讨论、去追求各种城镇化目标是有风险的。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实际面临的问题很大,竞争没有被清醒认识。我前一阶段去了一趟拉美、墨西哥,我8年前去过墨西哥,现在又去,感觉变化太让人吃惊了。从飞机上看下面的墨西哥城,以为到了中国的浙江省,工业厂房连成片,全是蓝色的厂房屋顶。我们很多人在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时候,其实对整个世界的观察是不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墨西哥人均的成本是6.5美金一小时,中国现在的成本上升很厉害,已经是6美金一小时,和墨西哥就差5毛钱。假设美国是一个中国的主要市场,它会选择近在咫尺的墨西哥还是选择万里之遥的中国呢?这个结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撤资潮。刚才张维迎老师讲到10年的窗口期,我们估计的时间也差不多。希拉里说中国20年后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句话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是在用奔跑的速度冲向地狱。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夸张,但是也描述了现实当中的一种倾向和可能性,这是不能回避的。如果我们不重新塑造自己对制造业的信心、对经济增长的信心,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难道我们还选择搞房地产?就算农民问题解决了,就算土地问题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有了土地、资本,我们要干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
再比如像老龄化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老龄化?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前一阶段我记得有一位部长级的干部在讲,现在老龄化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老龄化这个争论依旧很大,这种争论的背后还涉及到庞大的资产。我们中午讨论这个问题时提过,计生的罚款就有500亿,这一笔巨大的资产在改革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是问题。所以老龄化究竟有没有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一条不明确,改革方案的形成并保证有效就很困难。生孩子不像动物似的,猫三狗四猪五羊六,几个月就生一窝,现在只有在10几年20年以后劳动人口才能接上,这些孩子才能变成劳动人口,所以实际上现在已经晚了,只能通过国籍法的修订把中国转化成一个移民国家。如果这些都不去正视,还认为可以坐而论道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危险的。
环保是另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环保问题的愿景和现实存在巨大的体制性落差。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官员们都在大谈环保,讲多么、多么支持环保,为环保费了很多心血。但其实环保部门现在是“保生产”、“保增长”的主力,往往舆论揭露出环保污染事件以后,第一个大怒的居然就是环保部门,意思是根本就不应该揭露这些问题,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这种现象都是普遍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证明我们确实有一些前提性的重大问题没有讨论,而是直接就在讨论一些稍微让我感觉有一些虚的问题,这样下去是没有现实前景的。
我个人认为,改革还是可能存在重大政策风险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有负面的冲击,现在或许还未到改革大出手的时刻,需待根本性问题讨论充分,基础条件具备了,才能开展系统的实质改革。
现在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政策风险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改革方案和改革过程当中,相当冲动,搞的不好,我们政策中心CPU(中央处理器)很容易就出现溢出。轻易出台若干政策,搞不清楚这些政策导致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祸水,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案例出来了。比如说前一阶段的“国五条”,从市场角度来看是比较突然的,放出来之后,离婚率增长了不少,房地产交易大厅挤成一锅粥,房价不但没有降下去,反而大涨,股市出现了暴跌,当天进场托市的资金就是550亿,政策成本还是非常高的。我想现在可能还不到改革出大动作的时候,虽然大家对改革的期待还很多,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已经盼了很多年。但是总体上看的话,改革的大动作出来还不到时候,甚至谨慎一点说的话,现在的情况,也许改革措施越少出台越好。只有当这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之后,那样才可能对我们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市场利益,更为公平,更为透明,支持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