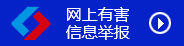口述者:宋晓梧
访谈者:肖冬连、鲁利玲
时间:2008年9月27日
地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宋晓梧办公室
整理者:肖冬连
我先后参与过劳动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或政策设计工作,我感到最难搞的是医疗保险,真是世界性难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西的九江和江苏的镇江进行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简称“两江”试点,成立了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改革领导小组,国务委员彭佩云任组长,几个主要部委分管的副主任或副部长任成员。下面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放在体改委。
我讲一个小插曲。1994年开始搞“两江”试点,劳动部和卫生部各抓一个点,劳动部侧重九江,卫生部侧重镇江。劳动部认为,这件事情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劳动部牵头;卫生部认为,这是医疗卫生问题,应该卫生部牵头。到了发文件的时候,两家为了文件上谁的名字排在前边争执不下。后来,听说佩云同志生气了,坚持把医改交给体改委牵头。当时铁映同志还不愿意牵这个头,但佩云同志还是坚持。这样,我调到体改委任社会保障司司长就自然兼任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医改办的副主任有体改委社保司副司长乌日图、劳动部的胡晓义、财政部的杜俭、卫生部的蔡仁华,后来又逐步扩展到药监局、经贸委、国家计委等单位参加。
医疗保险的决策分歧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始,也要搞一个大账户,后来考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太一样,各方面反映强烈,就搞了一个比较小的账户。“两江”试点和后来50多个扩大试点城市的经验,大多数都是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职工缴费在起步阶段为本人工资的2%,单位缴费比例控制在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自己缴的2%完全进个人账户;企业缴的6%,按30%比例进个人账户,剩余部分进社会统筹。小病由个人账户支出,住院了大病可以到社会统筹基金去报销。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当时医疗费用大幅度超支,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堪重负,财政也负担非常重。从1978年到199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医药费用大概上涨了28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保险问题,涉及到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财务体制。医疗保险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它不像养老、失业保险那样,退休人员领了养老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不是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而是医生说怎么花,才能怎么花。这就涉及医生的行为是不是端正,医院的行为是不是端正的问题。两江试点和扩大试点的经验说明,不合理的大额医药费用以及检查费用之所以产生,主要责任不在患者,而在医生、医院的行为扭曲。深入研究医生行为、医院行为,又是一大堆问题。医院要买药,又涉及到药品的流通体制和生产体制。所以,医疗保险很复杂。西方国家药品生产市场化程度很高,医院的管理也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制度,他们侧重研究医疗保险问题就行了。我们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医院管理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都在摸索,都是不稳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交错在一起,使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非常复杂。
改革开始是从医疗保险入手的。开始对医疗保险要不要设个人账户,也有过很大争论。镕基总理早期是坚持大个人账户的,后来他变了。1997年底,朱镕基听我们汇报。会上,朱镕基提出:“个人账户不一定搞那么大。”那时候,他还是副总理。佩云同志就说:“镕基同志,上次就在这个会议室你说要搞大个人账户,大家都听见了。”朱镕基有点下不来台,他不好冲着彭佩云发脾气。但等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发言后,朱镕基忽然冲他大发雷霆,说:“我说话,你们就当放屁!本来我就不爱管这件事,是你们让我来过问的。我说了,你们又不听!”他说:“我看就这样,单位缴6%,个人缴2%。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陈敏章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了。”单位缴6%就这么定下来了。当时,彭佩云捂着脸坐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她知道朱镕基是冲她来的,如果再争下去,非吵起来不可。会后,彭佩云和她的秘书姚晓曦商量,6%很多城市不够用啊!是不是再给镕基写个东西?最后文件上写的是单位缴费6%左右。
1998年初,讨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初稿时,在大都饭店开了一次医改领导小组会。那时,彭佩云同志已经确定不再担任国务委员了,会议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张左己主持,我还是医改办主任。我提出:“两江方案不是很成熟,医改问题很复杂,一些关键问题还说不太清楚,是不是再反复比较,酝酿一下,不急着出台决定。”会上有人说:“新政府一上台,要有政绩,出台这个文件恰逢其时。”张左己看我对尽快出台文件的态度比较消极,当场拍板,文件起草工作由医改办一位副主任负责。我从这个会议之后就实际上被免去医改办主任了。1998年政府换届,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务院医改办人员都合并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是不要我这个主任,只有我留在国务院体改办。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998年底,《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出台。这个文件出台比较仓促。这里,我并不是否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我只是认为,有些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报告,说医改总体不成功,这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有人知道我当初不赞成仓促出台医改方案,找到我,大约是希望我也说两句否定的话。我说我不赞成医改总体不成功的结论,更不同意撇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背景,简单拿建国初期50年代的数据与现在比较。与其说医改总体不成功,不如说医改滞后于经济改革,进展慢了,力度小了。我当初不赞成过早出台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现在不赞成否定医改的原则和方向。主要是我感觉“两江”试点反映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即时支付的医疗保险险种,是不是有必要搞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搞个人账户有它的道理,当然也有人反对。但养老保险是积累性的,不到60岁不会用,这笔钱可以拿去保值、增值。而医疗保险则不同,你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得病。尽管从概率上来看,二三十岁的人得病的比例要比五六十岁的人少,但就个人来说则很难讲。设了个人账户,会大大增加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加大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
关于最初在医疗保险中设个人账户的问题,我判断,劳动部不会提,卫生部也不会,还是体改委提出来的。我记得,李伯勇和王建伦都说是体改委提出的。好多人都这么说,体改委怎么那么迷上了个人账户。在国际上,医疗保险基本上没有设个人账户的。2000年,我们找了各方面的国际专家在钓鱼台开会,讨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也就是要在辽宁搞的试点。当时主要讨论失业、养老、医疗保险问题。第一是完善失业保险,把企业内部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逐步撤销,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并轨,国际专家没有人反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企业内部还搞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中心,这到底是企业,还是社会保险机构啊?再这么搞下去,很多国有企业就变成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了。企业的经营者要管职工养老,管失业,生产经营就顾不上了。第二是关于养老保险要不要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大是小,国际专家分为两派。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你最好不要搞个人账户,要搞也搞个小的个人账户。世界银行专家、智利专家主张搞个人账户,大账户,然后再经营运作。两方面的国际经验都有,国际上争论半个多世纪了。第三是医疗保险问题,与会专家没有一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搞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然而,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里了,后来又写在国务院方案里了,“两江”试点之前就写进去了。要改中央文件很难。
那时候,我讲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在一次会上,佩云同志说:“宋教授,宋教授,你现在已经不是教授了。”我理解,她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是国务院医改办的主任,不能发表质疑国务院决定的话,你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官员,必须执行国务院决定。以后,我在公开场合从不讲质疑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意见。但我一直担心搞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弊大于利。要不要在基本医疗保险里搞个人账户,应该深入探讨。至今,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建议把个人账户转到补充保险去。
谈到《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还应当提到一个执行中的问题。这个决定不只是针对企业职工的,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时,为了避免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不平等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覆盖城镇所有职工的新型医疗保险。再说,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一样,一个家里的人,我有保险你没有,可以以我的名义拿药给你吃。医疗费用的黑箱转移很难控制。尽管1998年出台了国家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实际上机关公务员至今没搞,事业单位也多数没搞,中央各部门至今没有缴费也没有建立个人账户。中央政府郑重推出的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只有企业职工在实行。你既然说好,为什么国家公务员不参加呢?而且文件上明明写着1999年底要统一,为什么不按文件办啊?因为实际上公务员的医疗待遇高,参加医疗保险个人就得交钱,而且待遇会相应有所降低。当时规定,副部长以下的全参加,正部长不参加,因为正部长有医疗保健。我们到海南去的时候,时任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表示他要在海南带头参加医改。他说:“谁说正部长不参加,我就参加!我就拿医疗保险卡去医院看病。”当时设计,副部长还是有专门的区域看病,不用排队,住院有单人病房。但哪些该报销,哪些不该报销,基本和老百姓一样。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大不一样了。医疗保险里的特权反映特别突出,但是没办法。你中央不是部长不参加吗?那到了省里,局长就可以暂不参加;到了市里,处长就可以暂不参加。一暂时就10多年了,你让老百姓怎么说!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定后,国务院开始抓相关的配套改革。李岚清副总理负责,抓医疗保险、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当时叫“医、保、药”三项制度改革。岚清副总理在1998年8月的一期《群众反映》上批示,只改医疗保险,不搞医院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药费是降不下来的。国务院成立了部际联席会议,还是要体改办牵头,我又成了工作班子的负责人。参加部际联系会议的单位有8个,体改办、计委、经贸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药监局、中医药局。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分歧最明显。调研时,有的地方两个部门负责人当面相互指责。卫生部门说是药商腐蚀医院,医药代表直接给医生开药品销售提成。药监部门,特别是医药公司的,说医院垄断药品销售,致使药品生产流通企业不得不贿赂医院,是医院变相索贿。有一次双方争吵激烈,卫生局副局长激动得犯了病,当场吃硝酸甘油。我主持会议,赶紧让他休息。经过部门之间的争论与妥协,也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医学界、经济学界和医院院长的意见,2000年最终出台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医药分开、营利性医疗机构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分开、调整卫生资源配置、实行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发展社区卫生组织、规范财政补助范围和方式等改革方向和措施,现在回顾,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改革的方向也对头,可惜贯彻落实不力,原定与这个指导意见配套的若干具体改革方案,有的还没来得及出台,2003年政府换届了,又遇到“非典”,注意力转到加强公共卫生,医药的“三项改革”实际被放下了。以药养医的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如哈尔滨“天价药”丑闻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医患矛盾加剧,到2005年有人提出医改总体不成功的论断,得到群众广泛认同也不足怪。
2000年,城镇“医、保、药三项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出台后,岚清副总理说:“城镇医药改革方向明确了,马上着手研究农村问题,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还是由体改办牵头,我仍然但任工作班子负责人。从2000年开始,我们到8个省的农村调研,看到农村卫生院破败的情况,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我对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之大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从1972年回北京后,再也没有到过农村。搞新型合作医疗大家都赞成,但争论也很多。最大的争论是当时财政部参加这个工作班子的同志不同意给“新农合”出钱,道理很简单,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跟农民自己合作,还是农民跟政府合作啊?既然是农民跟农民自己合作,政府为什么要出钱?我们说,这得靠政府支持、扶植和引导。一开始,卫生部想为全国每年每个农民向财政部要五毛钱的医疗费用,我们主张每个农民最少补助10元,现在盖个楼40亿、50亿不算什么,给这点钱不行吗?体改委副主任李剑阁说,每年每个农民给10块,全国最多就80亿,相当于修80公里高速公路。刘仲藜支持我们的意见。为这个问题我们工作班子有一次在杏林山庄争论到夜里1点多,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与妇幼保健司司长李长明气得血压升高。这个仗打一直打到李岚清办公室。记得当时岚清副总理主持,刘仲藜、高强、张文康和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参加,我作为工作班子负责人也参加了。最后,李岚清拍板:“财政出钱,中央出10块,地方再出10块,农民自己拿10块,30块钱起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时候,家宝副总理说了非常支持“新农合”的话。镕基总理担心,这个钱到不了农民手里,中间不知道被谁截流了。他的考虑也有道理。所以,镕基总理决定,先给两个亿搞试点,总算在2002年把“新农合”的文件出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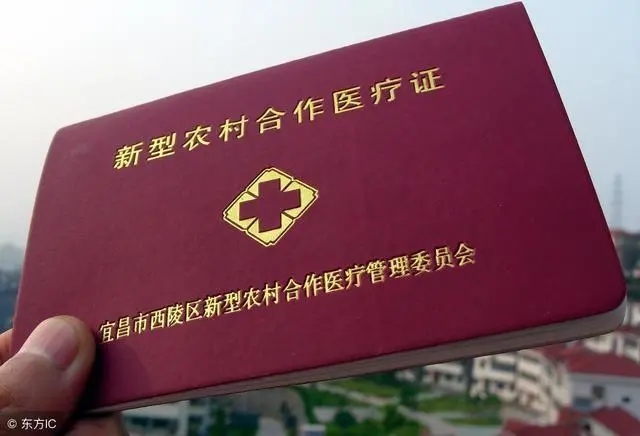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现在回顾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走了比较曲折的道路。我把社会保障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从1984年到1993年前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只是参与一些理论研究和学术争论。应该说,那一段社会保障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真是摸着石头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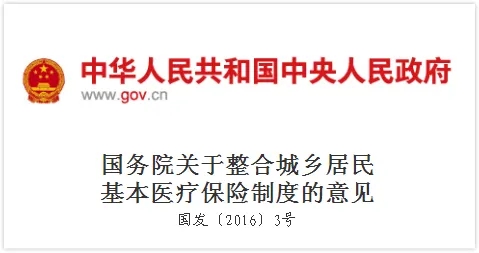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第二段是1993年到2003年,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思想就变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计划控制演变成宏观调控。当时,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包括五大子体系时,社会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子体系提了出来。社会保障理论地位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进入了体系框架构建阶段。从成就来说,这一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在框架结构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统账结合的制度框架建立起来了,管理办法确立了。1997年统一了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出台了医疗保险制度,1999年出台了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四个最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的制度框架都是在这一阶段构建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那种中央高度集权,委托单位管理,国家出资,低工资、高福利,主要覆盖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劳动保险制度。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社会保障改革仍然没有打破与国企改革配套的局限。我亲历的养老、医疗保险都是在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搞医疗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搞养老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而不是考虑怎么能够公平合理安排不同人群的保障。

城乡居民医保 “六统一”
第三段,2003年至今,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这个时候,社会保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才比较好解决了。如果停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心环节这个框子里,一些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现在,有些人否定医改,进而否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甚至否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挑出好多毛病。客观地讲,毛病确实有,但有它形成的历史原因,也有改革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原因。后来,我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文件的研究,但前期的工作我是知道的。我们在做“两江”试点时就说,先从企业职工搞起,然后是职工家属,逐步涉及城镇居民。镇江大概2002年、2003年就搞了全民的医疗保险。现在,医疗保险覆盖城镇职工2亿多人、城镇居民近1亿人、“新农合”覆盖8亿农民,还有一块医疗救助,从制度上说基本达到了全覆盖。农村也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些在社会保障作为国企改革配套措施的时候都很难提到议事日程。再有,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我们不仅要为过去没有被覆盖的贫困群体提供基本保障,还应当考虑适当消减党政干部以及国有垄断部门过高的基本保障水平,至少不要扩大不同群体之间基本保障水平的差距了。